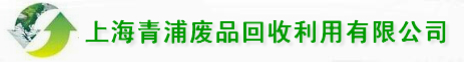被各方排斥的“废品回收站”才是真正的“垃圾分类专家”
2020/5/29 9:11:38 点击:
中国目前的垃圾分类公众教育仍然十分不够。这些“拾荒者”,变成真正的“垃圾分类专家”。
2017 年,北京共产生了约 900 万吨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万吨。这个数字还将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是确切地说,这 900 万吨里并不全是“垃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回收价值的“废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据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环境史硕士、环保 NGO “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估计:“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环保理念和政策都领先全美的加州,这个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说,这得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从 2013 年开始研究中国回收产业的维也纳大学学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调研中发现:在北京,这个“非正规部门”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废品,占城市全部废品总量的 74%。此外,它还回收了中国 60~80% 的电子废弃物,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撑起了这个正规产业。
潘介明发现,这个部门为政府节省了巨额财政开支,这在 2010 年是 4 亿人民币,2014 年达到 8 亿。而这还只是算了垃圾处理费用,若是把减少污染和节能降排考虑进去,节约的开支就更多。
这个没有编制,没有预算,没有工商执照的“非正规部门”,与政府旗下的环卫体系一起,构成保持城市清洁的两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来,这条非正规支柱却因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原因不断萎缩。而据潘介明统计,在 2011 年巅峰时,北京非正规回收部门的从业人员达到 30 万,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经急剧跌落到 15~17 万。根据陈立雯的调研,到 2016 年的时候,约一半北京骑板车的回收者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
当他们纷纷离去时,环卫部门的垃圾清运和处理量也在持续上升。陈立雯掌握的一个来自北京市环卫部门的数据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长率”达到 3%,这些没有人口和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废品。与此同时,被回收的废品的种类也在减少。
当每年数以百万吨计的废品因为得不到回收而进入城市的垃圾处理体系,它们被填埋、焚烧,或误入厨余堆肥场,将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同时,它们也失去了成为再生资源的机会,这让国家大力倡导的追求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无从谈起。
2017 年 7 月,中国政府宣布逐步减少进口固体废物(“洋垃圾”)的种类和数量。对循环经济产业来说,这既可以是危机,也可以是机遇。如果此时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国内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或可贯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么中国未来处理自己废品的能力将成为问题。海量的废品,将重归垃圾。
在谈及影响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其中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个退无可退的行业
晚上 9 点多,骑三轮收废品的何兴元与妻子回到住处,把板车停好,开始做晚饭。这是村里的一间用石棉瓦和铁皮搭成的简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块。冬天的时候,墙面会结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兴火灾之后,两口子就被从北京东五环外定福庄一个小区的地下室给“清理”了出来,他们搬来了一路之隔的村里。这间简易棚,就搭在房东自家屋后。可是,现在就连房东们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为“违章”而被大规模拆除,何兴元夫妇完全没把握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为房子嘛。特别是一大家子的,带着孩子,有的还是两个,很难找到房子,就自动走了。你看街上拉废品的车就能看得出来,少得多了!” 何兴元说。
李建军也留了下来,不过他的难处有所不同。见面的时候,他正在朝阳循环产业经济园卖废品,可他家却住在通州。他说原来在朝阳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里不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离朝阳熟客多的小区十几公里之遥,每天骑个三轮车,大把的时间花在路上。
哪怕侥幸没有被“拆违”影响到居住,货源也因它成了问题。吴东进父子在东五环外定福庄西街社区租有一间平房,门前挂块“收废品”的纸牌,安营扎寨,定点回收。这一带商铺多,还有一个老小区,过去生意好的时候, 2~3 吨的轻型卡车一天能装一车。但从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开始频繁上门,不允许外出回收,禁止门前堆放废品。8 月,附近街道开始“环境综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区也开始清退违建,不少隔断房的租户搬走了。现在,父子两三天才能收一车,只赚几百,远不如前。
2017 年,北京共产生了约 900 万吨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万吨。这个数字还将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是确切地说,这 900 万吨里并不全是“垃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回收价值的“废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据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环境史硕士、环保 NGO “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估计:“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环保理念和政策都领先全美的加州,这个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说,这得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从 2013 年开始研究中国回收产业的维也纳大学学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调研中发现:在北京,这个“非正规部门”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废品,占城市全部废品总量的 74%。此外,它还回收了中国 60~80% 的电子废弃物,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撑起了这个正规产业。
潘介明发现,这个部门为政府节省了巨额财政开支,这在 2010 年是 4 亿人民币,2014 年达到 8 亿。而这还只是算了垃圾处理费用,若是把减少污染和节能降排考虑进去,节约的开支就更多。
这个没有编制,没有预算,没有工商执照的“非正规部门”,与政府旗下的环卫体系一起,构成保持城市清洁的两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来,这条非正规支柱却因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原因不断萎缩。而据潘介明统计,在 2011 年巅峰时,北京非正规回收部门的从业人员达到 30 万,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经急剧跌落到 15~17 万。根据陈立雯的调研,到 2016 年的时候,约一半北京骑板车的回收者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
当他们纷纷离去时,环卫部门的垃圾清运和处理量也在持续上升。陈立雯掌握的一个来自北京市环卫部门的数据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长率”达到 3%,这些没有人口和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废品。与此同时,被回收的废品的种类也在减少。
当每年数以百万吨计的废品因为得不到回收而进入城市的垃圾处理体系,它们被填埋、焚烧,或误入厨余堆肥场,将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同时,它们也失去了成为再生资源的机会,这让国家大力倡导的追求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无从谈起。
2017 年 7 月,中国政府宣布逐步减少进口固体废物(“洋垃圾”)的种类和数量。对循环经济产业来说,这既可以是危机,也可以是机遇。如果此时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国内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或可贯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么中国未来处理自己废品的能力将成为问题。海量的废品,将重归垃圾。
在谈及影响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其中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个退无可退的行业
晚上 9 点多,骑三轮收废品的何兴元与妻子回到住处,把板车停好,开始做晚饭。这是村里的一间用石棉瓦和铁皮搭成的简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块。冬天的时候,墙面会结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兴火灾之后,两口子就被从北京东五环外定福庄一个小区的地下室给“清理”了出来,他们搬来了一路之隔的村里。这间简易棚,就搭在房东自家屋后。可是,现在就连房东们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为“违章”而被大规模拆除,何兴元夫妇完全没把握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为房子嘛。特别是一大家子的,带着孩子,有的还是两个,很难找到房子,就自动走了。你看街上拉废品的车就能看得出来,少得多了!” 何兴元说。
李建军也留了下来,不过他的难处有所不同。见面的时候,他正在朝阳循环产业经济园卖废品,可他家却住在通州。他说原来在朝阳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里不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离朝阳熟客多的小区十几公里之遥,每天骑个三轮车,大把的时间花在路上。
哪怕侥幸没有被“拆违”影响到居住,货源也因它成了问题。吴东进父子在东五环外定福庄西街社区租有一间平房,门前挂块“收废品”的纸牌,安营扎寨,定点回收。这一带商铺多,还有一个老小区,过去生意好的时候, 2~3 吨的轻型卡车一天能装一车。但从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开始频繁上门,不允许外出回收,禁止门前堆放废品。8 月,附近街道开始“环境综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区也开始清退违建,不少隔断房的租户搬走了。现在,父子两三天才能收一车,只赚几百,远不如前。
- 上一篇:上海废品回收开个废品收购站赚钱吗 2020/6/1
- 下一篇:2014青浦金属废品回收金属材料的硬度检国家标准 2014/8/21